百岁老兵30件战地珍藏,无声讲述着怎样的烽火岁月?
1952年元月。夜空翻涌着墨色,大雪如扯碎的棉絮,覆盖天地。入朝的晚上,杨伯飞肩头的钢枪挑着霜月,雪片混着冷雨,扑打在战士们的肩背与军帽上,凝成冰棱。一夜跋涉,这支队伍被风雪染成一片移动的雪丘。
拂晓时分,队伍悄然蛰伏于朝鲜村落边缘——蜷缩在低矮牛棚的暗影里,藏身于落尽叶子的枯林间。他们以班为聚,不惊动群众,不入民房住,咽下冻硬的干粮,隐蔽着做饭吃。暮色四合,当催征的号角撕破雪幕,队伍又重新没入黑夜中。
七十载光阴如鸭绿江水奔涌不息。后来,杨伯飞再也没有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朝鲜战场,那片浴血奋战过的地方。今年,听说江西革命军事馆正在筹建,杨伯飞托起了当年朝鲜民主共和国授予他的三等军功奖章,交付给馆藏时,他的目光穿越了数十年的光阴,穿过雨雪和烽火,直落鸭绿江心。“这些交给你们,我放心。”一同交付的,还有三十件他珍藏一生的军旅旧物。


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的一生,波澜壮阔,恰似江底深嵌的磐石——飞沙走石沉淀山河百年沧桑,民族精神的江河在血脉里永流不息。
杨伯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,三岁丧父,由母亲独自拉扯长大。童年时,黄坳村前田坞的老人们常说: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他记在心里,立志“用功读书,做个有用之人”,七岁入私塾,成绩优异。然而,现实的残酷击碎了求学梦——初中每学期35银元的费用,对这个家庭是天文数字。少年杨伯飞痛哭一场,无奈辍学,从此牧牛砍柴,分担农活。但那份“做个有用之人”的志向,从未熄灭。
1949年5月,22岁的杨伯飞迎来人生转折——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七团二营五连。从普通战士起步,他迅速成长。随部队在浙江省温州市、瑞安县、黄岩等地驻防治安,参加解放和清剿残敌浙江东部沿海岛屿的战斗。1950年,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敌前练兵中,作为突击班第一组长的他带头苦练,成绩优异,荣立三等功,并在战火中光荣入党。
1950年秋,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,以联合国军名义,由麦克阿瑟任司令率领,在南朝鲜仁川登陆后,越过三八线,分几路凶猛地将矛头直指鸭绿江方向进攻。麦克阿瑟扬言,“圣诞节结束前占领全北朝鲜,鸭绿江也拦不住联合国军前进。”他的声音顺着海风,散入仁川港咸腥的空气里。烈烈火光将新义州对岸的中国东北夜空染成深沉的橘红。中国人民志愿军奋起反侵略,于是年十月十九日入朝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。
急行军的昼夜在风雪里模糊了界限。渔陰山在望那夜,杨伯飞所在的部队在大山沟里沿着河水绕弯行走,冰河在脚下呜咽盘旋,一夜之间,二十八次涉过刺骨的激流。破晓前,到了两条河流开阔的交汇处——是敌机标定的死亡地域。杨伯飞奋力前冲时,脚下一滑,整个人连同沉重的装备摔入湍流。他挣扎爬起,起身跃跑扑上彼岸,栽进一坑洼地。几乎同时,数架敌机秃鹫般俯冲而下,疯狂扫射河面,许多在河中奋力前冲的身影,瞬间被殷红的浪花吞没。杨伯飞蜷缩在泥泞里,咬着下唇,感觉到胸膛里的心跳,咚咚地撞着冰寒的大地,身下的冻土仿在嗡嗡作响。
部队到达接防地后,担任二线预备队,隐入后方山沟。防空掩体与御寒的洞穴须凭战士的双手在冻土上一寸寸掘出。口粮是东北产的高梁米、小米、玉米粉和各种罐头,吃不上青菜,许多战士患上夜盲症。于是,在敌机盘旋的间隙,大家竟在驻地房顶和房前鲜土上,种下了白菜、萝卜、辣椒的种子——萌发出的微小绿意,是生命在焦土之上倔强燃起的火苗。杨伯飞回忆:“战士们为保家卫国,个个精神抖擞,斗志昂扬,不怕牺牲,毫无惧色。”
战争的风暴终究被挡回三八线以南。敌军司令换上李奇微又换上克拉克,都无法挽回败局。1953年夏,板门店的停战协定为硝烟画上句点。不久,时任连副指导员的杨伯飞,领受了一项沉甸甸的使命:收殓散埋四野的忠骨,修建陵园。起初,面对深埋的遗骸与浓烈刺鼻的气息,战士们裹足不前。杨伯飞没有言语,只沉默地挽起褪色的袖口,俯身掘开第一捧土。当指尖触碰到泥土深处的残躯,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个、两个……战士们默默加入,指缝嵌满深褐色的泥土。陵园里唯有铁锹掘土的闷响,混合着粗重的喘息、压抑的哽咽,在一片肃穆中久久回荡。半年光阴,逝去的战友们的英魂被迁入新坟,此后陵园移交给朝鲜人民军。那些年轻的名字,从此长眠于异国苍翠的山峦之间,与松涛为伴。
1980年,戎马半生的杨伯飞转业地方,在江西弋阳县、上饶地区饲料工业公司任职。他深入基层调研,落实建厂,为发展地方饲料工业倾注心力。
离休后的岁月,杨伯飞以笔锋代替了枪刺。在他的画作题诗中,始终如一的是那份源自烽火岁月的毅然与豪情。铺开素白宣纸,饱蘸浓墨,虬劲的枝干渐次蔓延。他题下旧句:“风雪严寒百物凋,独有梅花迎喜笑。”笔走龙蛇间,那画中梅枝的嶙峋铁骨,是当年战壕里冻僵的手指握紧钢枪的英姿,每一簇凌寒绽放的艳色,是战袍染血在雪地洇开的印记。“独步耸立嶙石上,傲视广阔原野间”,在硝烟未散尽的晨光里,无数英雄儿女“不爱红装爱戎装”,鹰隼一般立于焦土危崖上,眼底翻涌的不再是书生憧憬,而是淬过战火后刚铁般的信念和决绝。
当笔锋悬停,无论是那孤鹰傲视、征雁断翎还是骏马奔腾、满园春色,散尽的硝烟终凝成了纸上的万里寒香。杨伯飞老人常念及2027年军事馆开馆之约,届时若身体条件允许,一定要亲自走进这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场馆。也念及鸭绿江——不知七十年后的江水,是否还认得当年那个踏雪夜渡、九死一生的青年?
他想去看看自己捐赠的物品——当年并肩的大多数人不在了,光阴只留下了他的“老朋友们”,他要将这支精神的火炬,亲手传递给下一代。
他还想去看看那鸭绿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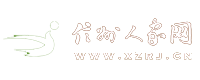





 赣公网安备 36110202000409号
赣公网安备 36110202000409号